邹元江:戏曲理论研究的拓展者——评《龚和德戏剧文录》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3-09-07
【摘 要】龚和德先生60多年来在舞台美术研究、戏曲理论研究、京剧艺术研究、地方戏及话剧演剧艺术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龚先生提出的当代戏曲工作者应肩负的保存古典的美、创造现代的美的两大任务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的,他对“现代戏曲”的质疑实际上揭示了这一观念的本质误区:放弃中国传统戏曲的文体结构,推崇西方话剧写实主义的演剧观。龚先生提出戏曲现代美的创造应包括“变革内容、解放形式”的双重蕴含是切中要害的,这显然是从当代的戏曲创造新的实践困境中被逼出来的真问题。龚先生提出的戏曲理论的研究要从维护性转向开拓性的看法也是引人深思的。既然戏曲理论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戏曲现代美的创造上来,那么,戏曲理论在戏曲危机中也应该从对传统的维护转向对现代的开拓。
【关键词】《龚和德戏剧文录》;戏曲理论研究;拓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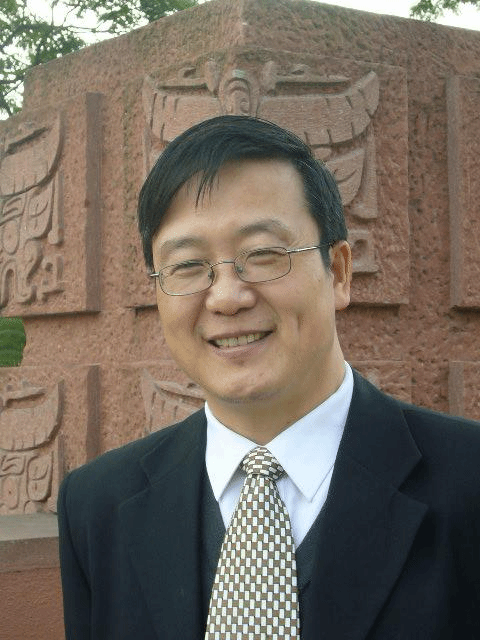
作者简介:邹元江,博士,yl23455永利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学、戏剧美学。
文章来源:《戏曲艺术》2022,(43)
龚和德先生1950年考入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舞台技术科(后改为舞台美术系),195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此开始跟随张庚先生参加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等重大课题有关舞台美术等章节的研究、撰写和修订工作。1991年退休后,龚先生从65岁开始又作为《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的常务副主任,兢兢业业组织编纂,直到2011年该书出版,他已经80岁了。20世纪80年代初,龚先生还受张庚的委派,从1983年开始筹备,直到1987年成立中国戏曲学会,他先任秘书长,后任副会长,发起并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设立了“中国戏曲学会奖”等。如今,进入九秩之年的龚先生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只用了两句谦逊的话加以概括:“在单位里,是个受集体科研项目培养、为集体项目尽心尽力的戏曲研究者;在社会上,是个多种戏曲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有时还是组织者、评论者。”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本专著,但却留下了400多篇长短文,包括“一史一论”的有关章节、两种“百科”的条目释文、专题研究、讲稿、各种评论、一些活动的宣传报道等。2020年底出版的《龚和德戏剧文录》就是他从中精选出的38篇学术论文和戏剧评论文章。这些学术论文和戏剧评论文章,除了第四部分是龚先生的本行舞台美术研究外,其他三部分的戏曲理论研究、京剧艺术研究、地方戏及话剧演剧艺术研究,都是他从1985年开始关注非舞台美术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
龚和德虽然跨出舞台美术本行研究开始关注戏曲理论问题相对较晚,但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奠基之作《戏曲前途与戏曲特征》和用力甚深的《中国戏曲——西方戏剧的重要参照》等文章外,1988年9月8日龚先生在中国戏曲学会召开的“探索性戏曲研讨会”上所作的《艺术探索与理论探索》的大会发言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
这篇论文针对当年如何面对传统戏曲遗产,又如何进行“探索性戏曲”的重大问题而极其敏锐的加以分析判断。该文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提出当代戏曲工作者肩负的两大任务:“一是保存旧的美,古典的美;一是创造新的美,现代的美。”那么,何为“古典的美”?龚先生认为,现在舞台上搬演的传统剧目,未见得都能表现古典的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古典美,也是要经过现代艺术家的精心选择和精心加工的。只有选择和加工,才是对于优良传统的最好的保存和发扬。”至于戏曲的现代美和古典美的关系,龚先生认为“不是一个替代一个、一个消灭一个,它们完全可以并存,可以在互相比较中既强化对方的价值,也使自身的价值得到肯定。”二是提出戏曲的现代美包涵内容和形式的双重蕴含:“变革内容、解放形式”。龚先生认为,“内容的变革并不是单纯的题材问题,关键是艺术家处理各种题材是否具有现代观念。”那么,何为“现代观念”?即今天的戏曲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看到一个动人的故事,“还希望从中获得一种新的认识,即能够帮助他们站在今天应有的思想高度,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进行思考。……所以,内容的变革是最重要的。”但龚先生觉得,“在今天,形式解放的难度和意义,似乎并不亚于内容的变革……形式不解放,新的表现内容很容易被扭曲”。所以,总的看来,龚先生认为:“形式的革新要有好的内容作‘灵魂’,好的内容一旦‘放在正确的形式里’,就会具有征服观众的强大力量。”三是提出戏曲理论的研究要从维护性转向开拓性。所谓“维护性”是指“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戏曲理论带有比较浓厚的维护、辩护性色彩,这主要是基于当时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从能否推动社会进步、开启民智的角度看待戏曲的负面性,片面的否定戏曲的美学价值,主张用“西洋派的戏”取代中国戏曲。而一些留学西洋的如余上沅、赵太侔等人,却从西方艺术当时正处在“反写实运动弥漫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家正在那里拼命解脱自然的桎梏,四面八方求救兵……在戏剧方面,他们也在眼巴巴的向东方望着”。有了这个参照,他们再审视中国的戏曲,得出了一些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之后,梅兰芳赴美、苏演出,西方戏剧家对中国戏曲“有缜密之追求,深切之赞叹”,这也增强了戏曲理论界的信心,于是成立“国剧学会”,齐如山等一批学者开始系统整理、研究、解释戏曲的美学内涵和规制……总之,这些针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洋教条的戏曲理论研究,在龚先生看来主要就是维护性、辩护性的理论,虽然“也为研究戏曲艺术的基础原理打下了基础,贡献很大,但也有欠缺”。所谓“欠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在总结和肯定传统戏曲的艺术特点、艺术规律时,更多引导人们关注的是古代,而很少考虑这种理论的现代意义。(二)有意无意告诉人们,似乎只要研究清楚了传统戏曲的艺术规律,吃透了传统,一切新的创作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可实际上传统戏曲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它所包涵的艺术经验肯定会对新的创造有借鉴意义,但解决不了现代戏曲的全部创作问题。(三)传统戏曲理论的研究者由于没有对现代戏曲的创作实践中的新问题引起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因此,这种对传统戏曲理论的研究就具有封闭性。而任何理论只有同新的艺术实践密切结合,才能保证它的开放性和富有活力。(四)这种封闭的研究多少助长了戏曲界的盲目乐观、守成和不思进取的情绪。因此,龚先生希望戏曲理论界要把注意力转向戏曲现代美的创造上来,戏曲理论在戏曲危机中也应该从对传统的维护转向对现代的开拓上来。
应当说龚先生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三个问题是引人深思的!长期以来,戏曲理论的研究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和各地方戏曲(艺术)研究所关注的重心在当代戏曲舞台创作所带来的现实理论问题外,绝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文学院对戏曲理论的关注主要是从案头之曲,即戏曲文本的视域做静态的学术研究,虽然也涉猎一些古代的戏曲理论问题,但绝大多数研究者很少看戏,更谈不上关注古代的戏曲理论在当代戏曲创作中所遇到的适用性或限制的新问题。虽然也有极少数学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余上沅、赵太侔等人对戏曲维护性、辩护性的理论进行研究,但也鲜有对这些理论从当代的戏曲创作新的实践中加以验证,尤其是加以理论建构性的探索。20世纪戏曲理论取得的最大收获或许是对包括龚和德在内的戏曲理论界基于梅兰芳访日,尤其是访美、访苏,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戏曲美学精神的解释,这是非常令人尴尬的!斯达克·扬、罗伯特·里特尔、阿特金逊、阿瑟·米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丹钦科、泰伊洛夫、爱森斯坦、布莱希特、戈登·克雷、奥布拉兹卓夫、桑顿·怀尔德、热内、格洛托夫斯基、乔治·巴纽等一大批西方戏剧家对中国戏曲艺术异域视野的阐释,虽然更增强了中国戏曲学界对戏曲艺术的自信心,但也由此而掩盖了中国戏曲理论界对自己本民族古典的戏曲艺术审美精神的失语状态,更遑论中国戏曲学界对当代戏曲现代美创造的理论探索和重新建构具有广泛解释性的理论框架。
龚先生提出的关于现代戏曲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变革问题也是切中要害的。过去戏曲理论界一直对梅兰芳新中国建立之初提出的戏曲变革要“移步而不换形”的看法非常重视,这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也即,内容是可以“移步”的,而形式是不可轻易“换形”的。这种执念显然也是从维护传统戏曲独特形式的视角出发的,仍没有跳出古典的戏曲艺术美学范畴。而龚先生提出的戏曲现代美的创造应包含“变革内容、解放形式”的双重蕴涵问题,显然是从当代的戏曲创造新的实践困境中被逼出来的真问题。古典的程式,都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马鞭(骑马)、船桨(行船)、走边(徒步)等表演程式到了当代都失去了生活依据,不创造适应当代生活的新程式显然就无法很好的表现当代生活。但要创造新的程式谈何容易,而且阻力也很大!龚先生认为最大的阻力一是求“像”,二是求“直”。所谓求“像”即京剧要姓“京”,评剧要姓“评”,演员要一招一式、一腔一调宗某派某师。但龚先生认为,“‘像’是一种摹仿行为,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不能对它强调得太过分;尤其对于新作品,更不能用‘像’去衡量,否则,就会抑制创作意识,裹足不前,永远搞不出新东西来。”所谓求“直”即在艺术上要找一条既不粗暴也不保守的笔直的正确道路,好让大家跟着走。龚先生认为,“这实际上是让艺术家‘走钢丝’,只能战战兢兢,走不好也走不快。”求直心切,总想纠偏,只会走向封闭。这些说法自然也有可商榷之处,但龚先生的本意就是希望古典的戏曲艺术能够在当代有所发展,在创新中能够传承下去,既然“戏曲的古典美是一种历史积淀”,那么“戏曲的现代美也将是一种历史的积淀”。而积淀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种种的“偏颇”,破格的尝试,由此而逐步形成观众认可的戏曲现代美的形式。这是很有道理的。
至于龚先生提出的保存古典的美和创造现代的美的当代戏曲工作者所应肩负的两大任务,更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孟繁树提出要“创造现代戏曲”的重要命题。这个所谓的“现代戏曲”并不是与古代戏曲、近代戏曲相延续的时序性概念,而是与“古代戏曲”相对应的概念。龚先生虽然肯定孟繁树的探索精神,但也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是“现代戏曲”的门槛定得太高,因而“现代戏曲”成了未来才能实现的“未来戏曲”。二是对传统戏曲在建设“现代戏曲”中的作用估计太低,似乎这二者之间没有一点转化的可能性。所以,孟繁树只赞成“两并举”(现代性和新编古代戏),不赞成“三并举”,断定经过改编的传统剧目进不了“现代戏曲”的大门。这让龚先生起疑:“为什么现代艺术家的现代观念可以作用于古代题材,却不能作用于传统剧目?创造现代戏曲,到底是观念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生活素材或艺术素材起决定性的作用?‘出身’不好的传统剧目一个也没有接受现代观念的改造的可能性吗?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太早、太‘绝’了?”三是“现代戏曲”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的“四个弱化一个强化”(即写意性、虚拟性、程式性、时空灵活性弱化,写实性强化)判断是否能成立。孟繁树认为“四个弱化一个强化”是现代人的审美意向和趣味,“现代戏曲”将按照这种框架去创造它的表现形式。龚先生则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单向性思维,是很不现代的思维,倒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19世纪末形成的写实主义演剧观的庞大阴影仍在他的背后起牵引作用。……我敢断言,现代戏曲的实践本身会打破这种单向思维。戏曲的审美走向,会从单向选择转为多向选择,或者说,这将是一种双向逆反中的多样化。”应当说龚先生的质疑是到位的,“现代戏曲”这一观念的本质误区在于,放弃中国传统戏曲的文体结构(“四个弱化”),而推崇西方话剧写实主义演剧观(“一个强化”)。新世纪初,吕效平接续孟繁树的话题认为,从1956年的《十五贯》、《团圆之后》到“文革”结束以来的《曹操与杨秀》、魏明伦剧作,这种新的戏曲文体已经形成。但这个新的文体如果从题材上将之称作“历史剧”、“现代戏”,或从剧种上称作“京剧”、“川剧”等都不合适,而应该称之为“现代戏曲”。显然,“现代戏曲”这个概念是很值得商榷的模糊概念,这是一个将川剧或京剧等等地域性的独特剧种的个性加以抹杀的概念,是一九四九年后“戏改”运动所遗留下来的突出问题的标签,即无视剧种的历史和限制一律都要编演现代戏,使之现代化。其实,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将戏曲西方戏剧话剧化,即故事敷衍非歌舞梗概化(而是话剧的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陡转、发现、高潮的亚里士多德化),叙述方式非戏曲诗性代言化(而是话剧的现代散文日常口语化),人物形象非间离类型化(而是话剧人物性格的个性化),表演方式非行当中介化(而是演员“进入角色”“体验化”),舞台空间非身段画景化(而是话剧舞美的逼真实景化),化妆装饰非表意脸谱化(而是话剧的日常生活化)等。毫无疑问,龚先生当年所担忧的传统戏曲美的赓续问题,近三十多年来已经被作为主流演剧形态的“现代戏曲”所遮蔽,成为文化主管部门所鼓励、所激赏,演艺院团和演员群体习焉不察所认同的“新传统”,甚至被褒扬为未来戏曲发展的新走向。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二
龚和德对京剧艺术的深入研究始于他组织编纂的《中国京剧百科全书》。除撰写了《试论徽班进京与京剧形成》《京剧故里是城南》等文章外,他主要是撰写了包括梅兰芳、周信芳、李少春、张君秋、赵葆秀等在内的京剧艺术家的研究论文。其中,《京剧老旦艺术的开拓——从给赵葆秀庆丰收谈起》一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戏曲形成时期没有老旦这个行当。王国维在《古剧脚色考》中说:“扮老妇者,谓之‘卜儿’。”作为脚色行当的老旦,出现于明代,成熟于昆剧。清代《扬州画舫录》把老旦列入“江湖十二脚色”,还记载了六名以老旦著称的演员姓名。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曲大辞典》在“昆坛人物·艺师名角”栏开列了465条传记,其中老旦演员只有10条。齐如山在《国剧艺术汇考》中认为:“专以老旦为主脚之戏,昆腔、弋腔、梆子腔都较少,皮黄班中则较多,故老旦一脚在皮黄班中亦较他班为重要。”为什么老旦到了京剧中才有了“较他班为重要”的地位呢?龚先生认为“关键是京剧的老旦行演员实现了唱腔的行当化。”正是从“京剧是在唱腔的行当化上最充分、最有成就的戏曲剧种”的视角出发,龚先生主要依据文献着重分析厘清了从龚云甫、李多奎、李金泉到赵葆秀为代表的老旦代际传承的重要问题。
龚云甫(1862-1932)之前的老旦“侧重于做工,唱的基本是老生腔,有些老旦唱功戏,常由老生演员反串。这个老生反串老旦的传统保持了很久,著名的有汪桂芬、汪笑侬、吕月樵、刘鸿升、高庆奎,一直到晚近的李宗义等。”京剧较早在老旦声腔上引人注意的是郝兰田(1832-1872),他也原是唱老生的。王瑶卿在《先外祖郝君兰田小传》中云:“三庆部方阙老旦,先外祖乃改老旦焉。时老旦唱法呆板,先外祖运以花腔,坐客大悦。”沈容圃所绘的“同光十三绝”戏装肖像集锦中有他所演的《钓金龟·行路》饰康氏的画像,可想当年郝兰田也是名动京华的一代老旦。但龚先生认为,“真正给老旦的行当唱腔奠定基础的重要人物是龚云甫”。依据是什么?龚云甫同郝兰田一样,原也是唱老生的,不过龚云甫是票友,是经孙菊仙识拔而搭入四喜班,并据其嗓音让他专攻老旦,介绍他拜四喜班老旦名家熊连喜为师。龚云甫之所以后来成为京剧老旦的一代宗师,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以老旦演大轴戏者。齐如山说“百余年来以老旦演大轴者,只他一人。虽然没有什么创造,但老旦的硬头戏都能唱,且有精彩,可惜四十岁后,嗓音很容易哑,嗓音痛快的时候很少,所以谭鑫培说,龚云甫奉官哑嗓子,我们嗓子哑,台下叫倒好,他嗓子哑喽,观众认命。语虽幽默,然确系实情。”龚先生认为,“能以老旦唱大轴,嗓子哑了观众还同情、谅解,不叫倒好,这样的老旦演员而‘没有什么创造’,似乎说不通。”所以,龚先生进一步追问,龚云甫究竟有没有创造呢?答案是肯定的。
龚先生认为,“在用大嗓、老生腔的前提下,老旦唱腔的行当化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演员的嗓子要有‘童子音’‘雌音’,就是嗓子较嫩,清亮脆润;二是要对老生腔进行‘软唱’处理,即糅合青衣腔使之柔婉,但要避免过于妩媚以致失却老年人的特点;三是唱功上要吸收大嗓的‘擞音’和小嗓的‘落音’。‘擞音’是老生腔中常以喉底着力用气顿出的颤音,用刘曾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发音中来自咽喉的一种小振动’; ‘落音’是青衣腔中间歇或收尾处用以表现女性娇柔的下滑音。用这两种音来润腔,有助于加强唱腔的老年感和女性味,也有助于行腔的玲珑有致。以上三条龚云甫兼而有之,所以能使老旦之腔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脱离老生味儿而自成一格,‘开创了老旦唱腔的新纪元,使老旦在京剧行当中一跃而占据了重要位置’。龚云甫创造的新鲜别致的老旦新腔,使老旦原有的唱功戏提高了艺术表现力而受到观众的重视,由原来的‘前三出’变成压轴戏、大轴戏。”正因为如此,龚云甫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徐凌霄称道龚云甫“演贫婆则酷似佝偻老妪,演贵妇则堂皇名贵”,他的表演有一个“任何人皆不能掩过之优点”,即“对于剧中人之情境,有真挚之热感,而竭其全力以表演之”,“口眼身步无处不显其感吸力”。四戒堂主人甚至将龚云甫的创造精神与谭鑫培、王瑶卿相提并论,称此三人“正是戏剧之马丁·路德,非唯无罪,抑且有功!”翁偶虹说龚云甫是“老旦行中一支主流——龚派”。龚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很对。龚云甫之外还有其他老旦名家,但龚派是‘主流’,后来绝大多数的老旦都宗法龚派,其中最重要的是李多奎及其高徒李金泉。”
龚先生认为,李多奎(1898-1974)先唱老生,因变声改学胡琴,嗓音恢复后虽拜罗福山学唱老旦,但继承的主要是龚派。1928年,平民在《谈老旦》一文中说:“近日路五为大舞台李多奎操琴,兼任教授,程、贯去后,多奎得蝉联演唱,路五之功也。”龚先生据此分析道:“文中‘程、贯’指程艳(砚)秋、贯大元,李多奎是随同他们赴沪演出的;‘路五’为陆五之误。陆五即陆砚亭(一作彦廷),是龚云甫的琴师。龚派之形成与陆五之成为‘拉老旦之专家’实是互相造就的。陆五对李多奎既当伴奏又当教授,将龚腔倾囊相授,梨园行叫作‘师傅胡琴’。”龚云甫在世时,李多奎已开始走红。红叶在《戏剧漫谈》文中曾总结“李红的原因,占着三点:一、有一条好嗓子;二、有陆五的胡琴;三、无对抗的敌手”。但龚先生认为,“李多奎的嗓音与气质不同于龚云甫,故同陆五的合作也有某种困难。徐凌霄曾坦率地指出,李‘断不能尽舍其特长以就龚腔。陆于龚腔则习惯自然,变换不易,唱与弦之格格乎不相入盖已久矣’。陆五老去后,改由周文贵(1911-2000)操琴。李多奎的特长得以发挥,遂在龚派基础上形成新的流派,世称李派,或称多派。据说,龚云甫‘腔无嘎调,罕用垛板’,而在李多奎最称拿手。由于他气力充沛、嗓音亢亮,更加讲究气口、喷口的运用,使得老旦腔的技巧性更强,韵味更醇厚,尤其在苍劲感上堪称极致。”因此,李派的影响至巨至深至远,后世唱老旦者几乎无人不受其熏陶、滋养。
龚先生认为,李金泉(1920-2012)就深受李多奎的影响,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艺时已是实习演出中的当家老旦,1941年后又以爱徒兼义子的双重身份受到李多奎的亲切传授。他“远宗龚派,近学多派”,根据自身条件和艺术理想,不仅学李多奎,“还重视追本溯源,综合创造而自成一家,有‘小李派’或‘新李派’之称。这同他不到三十岁就进入新时代,身处中国京剧院这样的创作环境有密切关系。……他既是男性演员创造的老旦艺术的一个完美的终结者,又是女性演员传承、拓展老旦艺术的积极推助者和杰出指导者。”龚先生说这是他对李金泉的“历史定位”。说“终结”,并不是说李金泉之后再没有男老旦了,而是老旦由他开始,之前以男性为主体,之后以女性为主体。说“完美的终结”,是指“李金泉勇于突破老师重唱工而不重念白、做工的局限,并在唱腔上继续进行女性化探索。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可说是隔代传承了发扬了龚云甫的优良传统,并给老旦艺术以新的时代风貌。”
龚先生认为,李金泉的重大成果“一是帮助高玉倩完成了《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塑造;二是精心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女弟子,以赵葆秀最为得意。”赵葆秀正是在李金泉手把手的传授下学演了李金泉与袁世海的经典剧目《李逵探母》后成为引人注目的老旦新星的。她与李金泉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并于1981年春正式拜师学艺。随后几年,两出老旦担纲的大戏《八珍汤》《金龟记》在李金泉的亲自指导下加工完成,成为日后赵葆秀的常演剧目。也由此,赵葆秀成为老旦行第一个梅花奖得主(1988年),梅兰芳金奖得主(1994年),文华表演奖得主(2000年),2007年还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在京剧界能获得四项殊荣的仅赵葆秀一人!
徐凌霄曾言及京剧艺术家有“模型派”(如钱金福、陈德霖、王福寿、何桂山、罗福山等)和“样子家”(如王瑶卿、谭鑫培、杨小楼、金秀山、龚云甫等)的区别:“模型派注重‘守规矩’,有天才有雄心的人,却时时刻刻想‘出样子’。”徐凌霄认为“样子家”更值得称赞:“自我作古,与众不同的‘标劲儿’,是他们成为特殊人物的原动力。他们的心里,都暗含一种‘规矩非为我而设’的傲态。”但龚先生却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他希望“京剧名家更自觉地既做‘模型派’,又做‘样子家’。”他之所以既看重“模型派”,也鼓励“样子家”,是基于当下的戏曲现实已经不同于徐凌霄提出此问题时的20世纪40年代初的状况。当时的戏曲,尤其是京剧虽是人才辈出,但剧目是以古典戏曲为主体的,因而长期观演“高等大路”的“模型派”的表演,既带来伶人表演的抱残守缺,也给观众带来不断重复的审美疲劳。所以,面对“程式的旧剧”,徐凌霄认为“需要出样子的人”来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而龚先生面对的却是21世纪既要传承古典戏曲传统,又要创造新剧目以弘扬传统戏曲精髓的双重任务,所以,他主张“对于优秀的传统剧目坚持做‘模型派’,但又要避免满足于‘高等大路’,争取‘深入戏情,能运用技术’,给角色以‘新生命’。若能持之以恒地追求,也有可能‘出了样子’。对于新剧目,则要尊重京剧是‘程式的艺术’,争取把它演出‘样子’来。但究竟是不是‘样子’,全在能否保留、有无传承。”显然,龚先生的辨证思考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
当然,龚和德最见功力、最娴熟的研究领域还是他的本行舞台美术。龚先生最初对戏曲舞台美术的研究是基于他的话剧舞台美术的学习背景,他最早的一篇戏曲舞台美术的研究论文《关于京剧的艺术改革中舞台美术的创作问题》就是他初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旁听梅兰芳、程砚秋、老舍、吴祖光、马彦祥等人参加的戏曲艺术改革座谈会,对其中所涉及的戏曲用不用布景问题的思考。梅兰芳说“活的布景就在演员的身上”,龚和德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文中竟然主张“应当把演员身上的‘布景’卸下来让给舞台美术来做”。显然,这个让张庚觉得“很勇敢”的论文一经发表,就受到戏曲行家的点名批评。没想到张庚惜才,从此文看出了龚和德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思考能力,便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其实,龚和德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前三十余年主要用功在戏曲舞台美术领域,除了已被收录到“一史一论”的有关章节、两种“百科”的条目释文外,他还在《文艺研究》和《戏剧艺术》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布景艺术三题》《现实主义多样化民族特色——关于布景艺术的回顾与展望》和《有个性的中性处理》等几篇重要论文,其中,《梅兰芳与舞台美术》一文是有代表性的。
该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梅兰芳在舞台美术上的突出贡献:一是完成旦角化装的新旧过渡。龚先生认为,“近百年来,戏曲的旦角化装,经历了由旧式向新式的演变过程。上海的冯子和等人起步最早,而把它完成的则是梅兰芳。”1913年,19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他对沪上的改良新戏以及新式舞台、新的灯光、新的化妆方法都非常敏感,甚至认为这是他“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回到北京后,他就与梳头师傅韩佩亭“细细研究”,“在眼圈、片子方面”“采取了一部分上海演员的化装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尝试和改进。龚先生认为,“比起冯子和来,梅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确定了新的脸型——鹅蛋形。在梅的前辈那里,化妆脸型基本上是方的。梅受了上海的影响之后,在摸索过程中,一度贴成了枣核形;最后他才找到了鹅蛋形,成为适应当时观众审美需要的最美的脸型。(二)在片子的用法上,按照老规矩,青衣很少用‘小弯’……经过梅的倡导,不论青衣、花旦、刀马旦,都把‘小弯’与‘直条大鬓’结合运用;‘小弯’由原先的一个或三个发展为五个、七个,这就丰富了旦角额部的线条变化,并同生、净等脚色的额部线条明确地区别了开来。……梅的改革,不仅影响了京剧,也影响了其他地方戏曲,成为数十年来戏曲舞台上最流行、最优美的化装规范。”龚先生的这个结论甚至可以得到国际上对梅兰芳评价的佐证。1930年美国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杨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就曾说:“我当即注意到梅兰芳的化装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
二是为美化古代女子另辟蹊径。梅兰芳从1915年开始为了结合一批新剧目演出歌舞并重的新风格剧,他参考了古典绘画和雕塑的造型,创造了一种美化古代女子的新的服装、化妆系统。这些被称作新古装的戏服“并非形式上合乎古式,不过京朝派戏中,初无此种装束,无以名之,故曰‘古装’”。虽然欧阳予倩与梅兰芳在同一时期也尝试过这种“古装”戏,但并没有引起注意,直到梅兰芳1916年第三次到上海演出,“以新装号召,然后相习成风,盛极一时,这可以说是京剧界一个大波澜”。那么,为什么梅兰芳的古装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呢?龚先生归纳了以下三点:(一)解放了戏曲舞台上的妇女发式。梅兰芳创制的新式古装,包括各种新型的发式和头饰,统称为“古装头”。龚先生认为,“古装头”不同于传统戏曲中汉族妇女都梳于脑后的“大头”(多用于夫人、小姐)和“抓髻”(多用于丫鬟及民间少女)之处在于,“古装头有个共同点:发髻多梳在头顶,不在脑后。髻形则各有不同,如吕字髻、品字髻、海棠髻、编髻等;编髻既可以正着梳,也可以歪着梳。头饰(又称“头面”)也随之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古代女性的高髻云鬓的美舞台化了,从而使戏曲舞台上的妇女发式多样化起来。”(二)开始注意表现女性形体的美。龚先生指出:“传统的旦脚上衣,如女帔、女褶,都很长很宽大,裙子系在上衣的里面。这种扮法,把女性形体的美掩盖了起来,梨园界戏称之为‘一统山河’。新式古装则相反,是上衣略短,裙子加长,裙子系在上衣的外面,从而加强了胸、腰部位的线条刻画,有利于表现女性形体的特点,更显修长婀娜。”(三)形成了崭新的装饰风格。这主要是指梅兰芳将传统戏衣“错彩镂金、雕![]() 满眼”的绚烂至极的美,趋向天然、淡雅的美。如梅兰芳扮演《葬花》里的黛玉和《浣纱》里的西施,头部主要讲究髻形的美,头饰用得很少,额前有看发,与“直条大鬓”结合着勾勒出俊俏的脸庞;服装剪裁合度,用料轻柔,用色淡雅,使人物显得格外清丽、潇洒。龚先生对此高度评价道:“看了这一类新式扮相,真使人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感。这种新的装饰风格,是对于传统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补充,为京剧人物造型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空气。”
满眼”的绚烂至极的美,趋向天然、淡雅的美。如梅兰芳扮演《葬花》里的黛玉和《浣纱》里的西施,头部主要讲究髻形的美,头饰用得很少,额前有看发,与“直条大鬓”结合着勾勒出俊俏的脸庞;服装剪裁合度,用料轻柔,用色淡雅,使人物显得格外清丽、潇洒。龚先生对此高度评价道:“看了这一类新式扮相,真使人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感。这种新的装饰风格,是对于传统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补充,为京剧人物造型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空气。”
三是提高传统扮相的艺术力量。梅兰芳一方面在新创的剧目中大胆创造新的人物扮相,另一方面,他对于自己常演的优秀传统剧目中的人物装扮也一直在做细致的琢磨和改进。他不赞成搞了新式的古装之后就“把优良传统的东西抛掉”,而主张“两者可以并存”,以利于戏曲舞台艺术的多样化。龚先生认为梅兰芳对于传统的扮相有小改,也有大改。大改最突出的就是《金山寺》中白娘子的扮相。也即将原来白娘子和小青都戴的“纱罩”(又名渔婆罩)改成大额子,不久又改成软额子。梅兰芳为什么要改戴软额子呢?龚先生认为,“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白娘子并非以女将身份出现,戴大额子缺少根据;二是白娘子在《水斗》时穿的是衣裤、战裙,并不扎靠,到了《断桥》时又换穿褶子腰包,戴了大额子显得头重身轻,并不好看。改成白色软额子,称白蛇额,配以面牌(又称‘整容’,专为能武者所戴),既减轻了头上的分量,显得匀称,又使白娘子的装扮有了自己的特点。”白娘子另一个重要改动是对面牌上的大绒球色彩由原来强调色彩的单纯素净的蓝色或白色,改为红色。龚先生认为,“一身洁白,头上一点红。这样一改,突出了白娘子的战斗精神。这是梅对这个人物有了新的理解之后的一种改动,提高了这个扮相的精神境界。确是神来之笔,十分精彩!”
四是对灯光、布景与后幕的探索。1914年,北京学习上海在新建的“第一舞台”开始使用灯光、布景,梅兰芳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在一些新排的时装戏和古装戏中采用了布景和灯光。龚先生认为,梅兰芳“把灯光的作用向前推进了一步,即由突出名角,变为对剧中人物进行‘特写’或制造某种气氛。1915年他排《嫦娥奔月》,演至第十场采花,就用了一道白光追照嫦娥。这是追光在京剧舞台上‘第一次的尝试’。” 梅兰芳对布景的运用,龚先生认为最大的贡献是在《洛神·川上相会》一场,即以一组高低三层的平台来作为仙岛的假定性形象,其“目的是要改变舞台的平面,使之多层次化,以突出、加强特定场面的歌舞表演。如此大面积地运用中性平台,在戏曲界,梅是第一人。”至于梅兰芳对后幕的不断改进,龚先生认为“他是更倾向于图案式的,但用的不是大图案,而是将花纹比较平均地布满画面,线条要纤细些,色调深浅要适中,避免反差太大,这样,近似于暗花锦纹,似有若无,既美化了舞台,又能突出表演。”龚先生以上这些细致深入的分析,都是很见功力的。
龚先生还在该文的最后一部分,对梅兰芳的舞台美术变革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加以概括:一是综合、平衡的戏剧观念;二是美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三是艺术创造是艺术修养的成果;四是同观众一道前进。这四点启示,把梅兰芳作为“美的创造者”、“感动国人之审美观念”作了系统的总结,尤其在文末,龚先生特别指出:“今天的戏曲界,无论哪一方面,都太需要梅兰芳式的革新家了!”透过此文,的确让我们深深感到,梅兰芳并没有远去。
